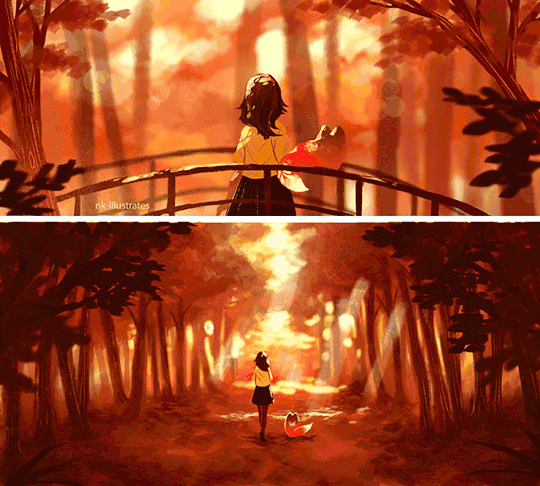她是我见过的抽烟最好看的女孩。修长的手指夹着烟,听你说话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吐个烟圈,一时像在微茫的雾气中。我给她讲课堂上老师的笑话,她斜着眼看我,将吸尽的烟头摁在烟灰缸里,很配合地“呵呵”两声,再感叹一句“真冷”。
那时我常常坐在阳台的椅子上看书,她穿着宽大的睡衣,叼着烟走过来,斜倚在椅背上,锁骨上的项链和她微微眯着的眼睛一样,透着一点狡黠。
在她还没学会抽烟之前,是爱着他的。
在更早的之前,她曾经问我,爱上一个人和忘记一个人,究竟哪个用的时间更长?我没有回答,但她后来就知道了,是忘记用的时间更长。
说到底,她遇见他,也就是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他在台上跳舞,长手长脚,但舞动起来却有野性。大屏幕上,能看到一双剑眉。音乐恰好来自她最喜欢的摇滚乐队——枪炮与玫瑰。
她那时候不会抽烟,不会化浓妆,清汤寡水的长发挂在还有点婴儿肥的脸庞。二十岁的一切,确实清淡,但比什么都新鲜。也无所畏惧。
因为晃动,大屏幕上他的脸有些模糊。她远远地看着,并没想走近,却明明在更远的地方听到了鼓声,像雷音一样,轰隆轰隆。可天地之间大白,还有一弯正遥遥升起的上弦月。她没意识到那是自己的心跳。
过了一会儿,音乐骤停,雷音却没停。
他那场表演正在谢幕。可旋即,一群女孩便围过去,拥到他身边。她怅然地看着一派花红柳绿,踟蹰再三还是踩着心里的鼓点声回去了。
在那之后,她才知道他也算校园名人,在各类活动中露面极多。她觉得这场相遇太晚,垂头丧气,尤其是得知连我这个宅女都对他略知一二时,她简直要叹息“君来我未来,我来君要走。”
不过正因为他在校园里出名,所以她没费多少力气就打探到了全部信息。听说他还没有女朋友的时候她很开心,可想到那一派花红柳绿又黯然,但这也没妨碍她一有空就去旁听他的课程,尽管那些课不是“岩土工程力学基础”便是“流体力学”,她一个都听不懂。可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主要是为了看他。
在一个理工科院校里,他所在的系才只有几个女生,所以尽管身边不乏女生追逐,他还是注意到了她频频出现的身影,何况她本来就长地高挑出众。
她一次一次打着上课的名义“偷窥”他,可有一次一不留神撞上他回头注视的目光时,她却突然胆怯了。齐刘海下一双眼睛四处躲闪,手里一本格格不入的《国际金融学》又不能举起来充当掩饰,如坐针毡了一会儿只好抱上书包,弓着腰从教室最后逃离。他看惯了其他女生落落大方的示意,反倒对她的犹豫和躲闪产生了兴趣,虽然她那之后再不敢出现在课堂上旁听,但他还是略微记住了她那个仓皇紧张的背影。
传说中有个理论,通过六个人就能认识全世界。当这个全世界缩小到校园时,需要的可能只是两个人。所以很意外的一次聚餐,同学只说有其他朋友,她竟在餐桌上正式认识了他,虽然第一眼看到他在座位上气定神闲地点菜时简直想逃跑化个妆再回来。
认识了之后,她终于可以明目张胆地做一切对他好的事情,虽然和她有同样想法的女生那么多。她等着他排练,为他的性感舞伴吃醋心酸。但他一个笑容递过来,她又在心里升腾出甜蜜的期待。
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当然不仅仅是看他发的每一条状态都像做阅读理解。
你等他回短信,像等一辆永远不会到站的公交车。你看天看地看远处的云,其实眼睛从未离开公交车驶来的方向。你听到短信提示音迫不及待地打开看,发现只是10086的时候叹着气放下。就算你等到最后也没等来那趟车,但还是找了一万个理由原谅他。
很多个时刻就在这样拉拉扯扯的纠结心思中度过了。有时候她觉得太难坚持,发誓就此删掉全部联系方式,可他的电话一打过来,所有精心堆砌的堡垒统统坍塌。
他对她是有不同的,因为她的单纯几乎让他卸下了全部防备。
有一个夜晚,他送她回宿舍,坐在宿舍楼下的长椅上聊天,他点了根烟,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话。所以她知道了他因为父母离异而倍感残缺的少年时代,也知道了他那些以为婚姻就是不幸的顽固念头。
她有一瞬间的慌张和失望,但还是问他,为何要对她说这么多。他只捏了捏她带着酒窝的脸颊宠爱地说:“因为你太快乐,让我在你身边都有了一种自己也很快乐的错觉。”
也许因为月光下的那一刻太美好,所以她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脱口而出:“要不你跟我试试吧。”
年轻时候的爱慕,有太多壮怀激烈的心情。总以为爱是拯救,能用温存将一个不愿停驻的过客感化成称心如意的旅伴。
可她终究没能改变他。
他们在一起了一年,甜蜜过后便陷入了家常便饭似的争吵。他身边的女生太多,有默默守望者,有公然挑衅者,在这场恋爱中永远都欠缺安全感的不是他,反而是她。不知不觉两个人都倦怠了。她不再是那个只会在舞蹈教室外沉默等待的温柔女孩,开始在察觉短信里、QQ上的一切蛛丝马迹之后跟他要一个合理的解释。他自诩问心无愧,她却只想他是自己的。一次剧烈的争吵之后,她喝醉了酒大哭,只说:“我只想他是我的啊……”
分手那天也是一个相似的深夜。
喧嚣校园里的人声都退去了。他坐在操场边的长椅上,脚边已是一地烟头。她气急败坏地将他手里的烟夺下,他颓然低头任她摇晃一动不动,她只好蹲到他面前,结果正看到他眼底泪光。她惴惴不安,感觉自己终于要等来那个宣判。
这次他还是轻轻地捏了下她的脸,她转身离开,什么都没说。她没有力气去擦满眼的泪,也不知道该怎么挽回,挽回那些日日夜夜的付出。
有人失恋,会找全世界去倾诉,因为语言也是情绪出口。但她没有,几乎对此一言不发。所以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度过了那段时间。只发现从某一天开始,她越来越能够娴熟地为自己燃起一支烟,我也渐渐习惯了房间里突如其来的烟味。
她常常失眠,我夜半醒来,还能看到她就着一盏微弱的夜灯看书,也许因为她更瘦了一些,所以书页上的纤细手腕愈发显得凛冽。
五月的天气忽冷忽热。有天大雨滂沱落下,我俩站在阳台,正看到楼下小花园里的玉兰花砸在地上,只留一地狼狈的白。她皱眉点起一支烟,叹了口气。
我便想起我失恋的那个五月也在下雨。急急地说完了最后一段话便铁了心转过身,打着雨伞低着头飞快地向前走。记起校园卡还在他身上,但我不愿回头,怕一回头便前功尽弃。眼泪和雨水混在一起,模糊的视野里只有自己的脚尖,可那鞋子还是和他同款的情侣鞋。所以我像个神经病一样在宿舍楼下脱了鞋袜扔进垃圾桶,然后光脚走回宿舍。
而那天之后的一个月,我和往常一样故作镇定地上课读书,在课间大声说笑,一个人坐空荡荡的夜车出门旅行。但更多的时候,在沉默的痛感之外,常常坠在恍惚的梦境中,很早就醒来,睁开眼却只看到天色青灰,窗帘的一角飘进来清冷的风,难以再入睡,只好等着晨光一点点亮起来。
原来时间不是杀猪刀,失恋才是。它让你变得面目全非,烈马被驯服,疯长的念头都变得整饬。
电影《等风来》里,程天爽说,我们最后都变成了小心翼翼的人。
从义无反顾到小心翼翼的路上,失恋无疑是最快的催化剂。
问过很多个失恋的人。
A说,半年多了,每当手机震动,或有短信的提示音,还是下意识地希望联系我的人是他。在路上看到相似背影,还是会突然紧张起来,不自觉地想逃开。仔细一看不是他,才略微地安心。
B说,那是一种整颗心都被撕裂了一样的疼痛。总之再不会翻山越岭,只为站在那个人面前,只为她一个惊喜的笑容。
C说,减掉留了十几年的长发,以为容貌坚毅自成铜墙铁壁,可谁也不知道,心底那块原本最柔软的地方已无人能侵。
D说,我告诉自己,就再勇敢和放肆这一次吧,我要试着走向他。可我没想到,走向他的路上全是突兀的刀尖和凌乱的碎玻璃。我回来了,不是因为鲜血淋漓的脚掌和万箭穿心般的痛觉,而是,我走到一半才发现,在指向他的路牌上,赫然写着“此路不通”。
当然,如果失恋是一场病痛,它不可治愈,但足够在漫长的时间里模糊最初的情绪。就连亦舒师太都总结了失恋之后的步骤。痛哭流涕、形销骨立、怒不可遏、慢慢遗忘,直至真正成为过去。
我也知道她的痛苦正越来越淡。不再流莫名其妙的眼泪,不再发出长而无力的叹气,也不再期待着拐过哪个路口能再遇见他,该以什么样的神态说着什么样的话会不会尴尬。所幸校园并不大,但重逢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有的人就是这样,一转身就是天涯。
后来,她也遇到过喜欢她的男生。其中一个格外用心,但她铁了心拒绝。有一次,看着那个男生在暴雨中走远的背影,她回来黯然,不是为他,是为自己。
她说,他就举着一面镜子,让我看到过去的我,看到舍身去爱的那个人有多卑微。
可谁让爱情从来不是对等的东西。甲之砒霜,乙之蜜糖,可有人宁愿万死不辞去做砒霜,结局却是甲乙终究都不得所爱。
她最终没有接受那个男生,尽管他的失魂落魄于她并非胜利者的勋章,反而像一粒苦药,每每遇见便像一场反刍。因为她知道那种苦涩如何难以下咽,更不愿同样的苦痛被施与别人。
可这世间,最勉强不得的便是人心。
所以她苦笑着说,总得撕心裂肺一次,才只好没心没肺,甚至狼心狗肺。
不知道你是否也和她一样,用几个月爱上一个人,却要用几年来遗忘,甚至用一生来反刍他给你的改变。尽管风还是风,河流还是河流,但你知道执拗变成圆滑,主动退为闪躲,你学会了巧笑倩兮,却难以露出一个心愿得偿后肆无忌惮的大笑。你也学会了伪装真心,权衡得失之后才做出一个暧昧的决定。
原来,是失恋连同时间让所有的柔软和不舍开始面目全非,我们才终于变得刀枪不入。
更后来的时候,她毕业工作,也谈过几场无疾而终的恋爱。城市太大,一个人的悲欢离合比尘土还微不足道,她渐渐就模糊了自己的面孔。
深夜加班过后坐在略显空旷的地铁上,她疲倦地看向车窗,玻璃上映出的面容带着深深的倦怠,再不是那个二十岁的无畏女孩,这种对视让她凛然一惊。她渐渐地感觉不再认识自己。
她也有过数次相亲,和只看过一张照片的人吃一顿无所事事的饭。中途有时会有片刻的失神,只看到对面陌生人张张合合的嘴,再回过神来,便难以想象该如何和此人结婚生子,唇齿相依地度过如蝇命般脆弱但一眼望去也尽觉漫长的人生。
她还在心里存着一份执念,觉得会有另一个人出现,就像那个有上弦月的傍晚轰轰隆隆的雷声一样。或者,她想着再退一步,不要雷声一样的心跳,但至少能让她遇见那个人时轻轻地松口气,在心里对自己说:“是了,就是这个人了。”
可是没有。
尽管她走走停停,和数不清的人群错肩,却未再无所保留地付与全部内心。有时站在早高峰的地铁门口,身旁人群喧嚣着像潮水一样流过,看着无数的面孔或焦躁或新奇或不安或雀跃,她不确定能在哪里遇到那个人,一回头,回忆也是一片空荡茫然,她的心底便发酵出了失意与灰心,甚至怀疑。
上一次见面,我们在外滩。身后的一片灯火渐次暗了,只剩下她的烟头还明明灭灭。大风呼呼地刮过耳际,她递一只耳机给我,歌是张悬的《关于我爱你》。
她熄了烟,给了我一个恍惚的微笑。我便想起更过去的时候,所有怀抱着的对于爱情最善意和单纯的期望。
我想,在必须发现我们终将一无所有前,一定有个人也在遥远的路上走着吧,带着无限的温柔和懂得,走向我们必须相遇的路口。
虽然你不曾莅临我艰难跋涉的孤独过去,和动荡不安的冷酷青春。甚至连我都要忘记自己是如何独自一个人走过了泥泞漫长的路程,又是如何将所有的残缺修补完整,将不安与疼痛收拾妥当。
但一定会有那样的一个时刻。
恰好在我想拥抱你的时候,你也愿意拥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