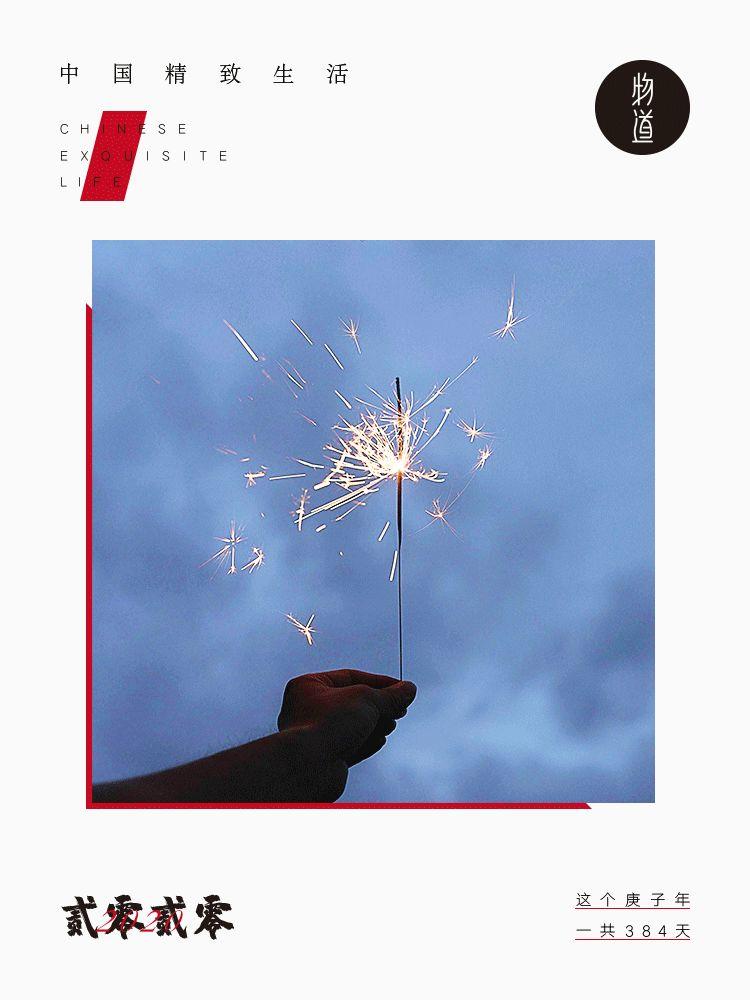物道君语:
没有无聊的人,只有孤独的灵魂。
2月10日,推特上有个人说了一句话:“好吧,美国宇航局今天说,这是扫把由于重力的作用而能够自行立起来的唯一一天。”下面附上他立扫把的挑战视频。
短短一天内25万个赞,然后病毒式地传播全球,刷屏社交媒体,俨然之前的冰桶挑战、踢瓶盖挑战。
而事实上这只是个谣传,美国宇航局辟谣,“让扫把立起来的基本物理学在每一天都有效。”
但在因疫情困居半个多月的中国,这谣言迅速成为快乐源泉,只要你够无聊(耐心),扫把就能立。
网友们赶在这特殊的一天开始挑战立扫把。立完扫把立鸡蛋、黄瓜、硬币、牙签、菜刀、雨伞、剪刀…..
其实是不是谣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真闲得无聊。而这小游戏是份简单易得的快乐,缓冲了每日微博上令人沮丧的热搜。朋友圈刷屏的同时,开心变得很简单。
快乐总是属于那些自得其乐的人。
也许生活本就没有无聊的事,只有不适应无聊的孤单人。
在无聊中,培养独处的精神
塞涅卡说:愚人饱受无聊之苦。
因为独处时,每个人都返回自身,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暴露无遗,诸如贫瘠的精神,乏味的个性,亦或者相反。
善独处者,善培养独处的精神,回归精神的宁静。
当木心独自被禁锢于监狱斗室之中,面临无尽的时间和噬骨的无聊。
但他独处时,却写了十余万字的《狱中手稿》,写作让他清晰,他在白纸上画出琴键,弹奏无声旋律,音乐让他宁神。
又或划一根火柴,倒插烟灰缸里,欣赏它寂灭的美感,如同一出戏剧,让荒芜的监狱充满了美:
“凝视着那木梗燃烧到底,成为一条明红的小火柱……忽而灰了,扭折,蜷曲在烬堆里……烟缸活像圆剧场,火柴恰如一代名优,绝唱到最后,婉然倒地而死……”
他对好友说:“看到处理现实生活的窘迫,我很无能。但我一回到书桌前就静了下来,我就是主宰,直通上帝。”
对会独处的人而言,闲散恰恰是一个人的清欢。
他们直面自我,心灵与天地万物往来,能发现细微之美,洞察人心之深,把无聊的日常活出诗意,甚至伟大。
在无聊中,重新审视自己
有这么一本书:《在自己房间里的旅行》,作者与当下的我们面临同样的处境。
他被关禁闭42天,在这短短42天里,他完成了这世界上最短的旅行,只有短短36步距离。他在房间里直走横走斜走随意走,用脚步丈量房间,用这平淡无奇的旅行经验,靠想象重新审视了自己。
同样的,佩索阿在《不安之书》里写道他想象的旅行:“在夜幕降临的亲切氛围下,面对着逐渐闪现的满天繁星,我踏上未知的、想象中的或通往完全不存在的国度的旅途。”
他说:若我想象,便能创造;若我创造,便能存在。
旅行是旅行者自身,你所见所闻不是景物,而是自己。
他是一个孤独的诗人,享受这份宁静和想象,并在找到自己的同时创造了多个“自我”。他在书中杜撰了近百个“异名”,每一个异名都给他编造了职业性格,身世甚至思想,栩栩如生,真如其人。
每一个都是他,是他清晰剖析自身的存在后创造的另一个自我。
审视自身,是需要跳脱被框住的思绪,当你没有了忙碌,没有烦扰,思绪放空后,你会发现你也很富有。
生活有乏味无聊的现实,但我们可以穿过这荆棘,抵达通透的自我。
旅行何需远方,审视不必拷问。
打发无聊最好的方法,是来一场面对自己的“旅行”。
在无聊中,重拾生活的信心
这段时间里,每日上涨的确诊人数,漫长无期的疫情拐点,无一不在消磨希望和信心。
我翻阅了《独居日记》,试图找到某种类同的经历。
作者梅·萨藤,一个老伴去世,罹患抑郁症的老人,在她的文字里却从容平静。
她说:“穿越痛苦的唯一途径是经历它,吸收它,探索它,确切地理解它是什么以及它意味着什么。”
这份无处不在的希望恰恰来自于她在日常生活里的探索。
如今生活秩序已混乱,我们所能着手的,无非从细微小事中把混乱变有序。
她提到一个素食者,在忙碌的全职工作之后,还花几个小时采摘蔬菜,一边做饭一边沉思,因为在她心中烹饪如同圣礼。
其他小事亦如是,如铺上干净的床单,如清理花园,把混乱整理为有序。
每当梅·萨藤厌倦烦闷之时,便整理花园。
“播种旱金莲花和金盏草,在要栽西红柿的旁边栽了一排万寿菊,清理了让飞燕草窒息的杂草和毛线稷,剪掉了篱笆上的一大捆枯萎的铁线莲,还有到处攀缘的蔷薇。”
对于她来说,园艺清空大脑,能恢复宁静,她能沉浸于此,等回到屋中时再次感到自己精神集中,重新成为一个整体。
不断把混乱变得有序就是生活本身。
因为那些平常的小事,需要极大的克制与自律,那是生活真正的考验。
疫情爆发后,斯洛文尼亚的哲学家齐泽克说了一个词:Holiday in Wuhan(武汉假日)
他提到了一个宣言:“无僵死时间地活着,无障碍地享受”。
僵死时间是疫情下的抽离时刻,有人懂得利用好这个僵死时间,从忙碌中脱离出来,思考其困境,重新唤醒生命活力。
也有人能够无障碍地享受着这称之为“宁静”、“释放”的时刻。
如何在无聊中寻找自我,如何度过漫长的时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但愿人人都能有足够的时间去回望与沉思。
往后余生,真正地无僵死时间地活着,无障碍地享受。